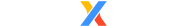编者按:5.18国际博物馆日,向在启行学社营会活动中以”展品“形式陪伴孩子们的志愿者致以感谢!我们期待启行学社的营会活动成为真实流动,双向观展的“人类博物馆”。
在2024年2月启行学社项目在郝堂的首次营地尝试中,项目组就提出了“人类博物馆”这一概念。
来自不同领域,不同身份,不同行业的志愿者化身“展品”,以三个标签定义自己。
孩子们可以选择感兴趣的标签,找到“展品”,随后在“展品”自己选择的“展厅”中,与孩子们展开对话,以提问和回答的方式“观展”。
图为2024登封冬季营人类博物馆志愿者张晨辉和孩子们
这种陪伴形式的缘起,是项目组发现有一些志愿者无法全程参与营会,只有1-2天的陪伴时间;此外,在踩线过程中,项目组发现营会所在地的居民中,也有经历独特,个性鲜明,且对于活动很感兴趣的潜在参与者。
如何让这些参与者在宝贵的营会期间发挥作用,Ta们应当承担什么角色,才既照顾儿童的主体性,又兼顾志愿者的多元性和参与热情?
经过讨论,项目组为这些流动的志愿者敲定了一个略带幽默感的命名:“人类博物馆展品”。
有些伙伴听到这一命名,表示有些“惊悚”,经过理念说明与信息同步后,“人类博物馆”就从内部梗,成为了启行学社志愿者分类的一个正式命名。
命名即意味着定义。项目组在后来发现这一偶然命名,通过身份流动、语言交互与关系的重新定义,超越了教育公益项目中“启蒙”与“被启蒙”的角色,将志愿者与儿童置于了共同的主体性空间中。
首先,将志愿者定义为“展品”,强调了儿童在其中的主体性。
其次,志愿者也并非被凝视的客体,标签、展示空间以及对话方式都是基于自己的选择。
当孩子们找到标签对应的展品,对话开始时,一段双主体之间的交流就地发生。
在郝堂村营地,孩子们需要根据标签和NPC对暗号后主动触发对话。
其中一位NPC的标签之一是“村官”,孩子们根据过往经验一直寻找年长男性对话,直到最后发现对上暗号的居然是一位青年女性。
孩子们说:啊?村官居然是女的?
志愿者姜佳佳说:村官是一份工作,当然男女都可以做啊。
张老师回答:“这跟职业没有关系,或许很多人都不了解自己,我只是愿意承认,承认了,就会探索,艺术创作是其中一种探索方式,你觉得还有其他探索方式么?”(大意)
启行学社一贯拒绝封闭式营地,倡导空间开放和选择开放,通过外部真实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打开身体的感知。
人类博物馆当然也是如此,志愿者们可以选择草坪、茶室、村舍等真实场景作为自己的“展示”背景。
在2024的郝堂冬季营中,郝堂的采茶人朴素先生、卖酱菜的杨二姐、饭馆老板四成以及开客栈的燕子姐等,都是在自己日常的生活环境中完成了志愿服务,服务内容就是展示他们的日常生活,并邀请孩子参与其中,一起交流心得。
2025年登封冬季营,小组探索时,孩子们与广场舞大妈、保洁员阿姨,打烧饼的师傅等生活与工作状态中居民进行了交流,志愿者在复盘时戏称这些交流为“人类博物馆临展”。
仅靠语言文字的传输,人无法建立真正的牢固认知,认知基础还来源于身体的感受与在场的体验。
当孩子们在采茶中聆听制茶人的分享,过视觉、嗅觉、触觉、疲惫等综合的身体感知,才能理解制茶人叙述中,对一片茶叶的成品所传达的理念与坚守。
只有具身认知,才能让抽象概念转化为肌肉记忆与情感体验,沉淀为为个人经验的一部分。
图为2024郝堂冬季营孩子们在朴素先生的茶室
每场营会的结营日,都会有大型的“人类博物馆”,长期志愿者也用标签来表达自己,邀请孩子们前来“观展”交流。有孩子发现,志愿者的标签和半年前完全不一样了。
观察到这种变化后,有的孩子会主动问:“你为什么改了标签?”志愿者就分享自己在这段时间内的经历和反思。
志愿者姜佳佳的标签从“村官”变成了“社工”
项目组内部也在持续记录着志愿者们标签的流动,并且开脑洞说或许到三年后可以做一个“展品标签回溯墙”,邀请参与者互动揭秘,看看标签背后是哪位志愿者的哪个阶段。
标签代表的是此刻对自己的理解,流动的标签则清晰地向孩子展示出:“自我如河流,此刻的你包含所有过往,又蕴含着未来的可能”。
有志愿者问我:启行学社培训时反复提醒我们拒绝使用“懂事”、“可怜”等词汇来标签化孩子,那为什么“人类博物馆”的展品要“标签化”自己呢?
我答:标签本身不等于标签化,如果标签是把一个真实立体的人变得单薄,那是标签化;如果标签只是开启对话的一个由头,目的是为了还原一个具备复杂情感的主体,那么这里的标签并非标签化,而是一扇推开更广阔世界的门。
人类博物馆的志愿者,每一个标签背后,还带着丰富的经历和深刻的思考,标签是起点,根据不同的孩子,不同的问题开启对话交流时,才会被激活真实的呈现。
他们有些从身份标签(村医)开启,结果最后孩子们愉快地聊起了个人爱好(钓鱼);有些用很抽象的思考标签(好奇),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职业(研究者);有些志愿者会选择暴露脆弱,分享自己高考失败的经历;也有志愿者在对话过程中被孩子们好奇的提问触动而落泪。
图为2025登封冬季营人类博物馆王增民老师与孩子交流
人类博物馆的目标不是找一些大人分享人生经验,指导小孩的人生,而是通过人本身存在的丰富性,打开通往世界的观察之窗,让孩子看见更多元的性格,更多样的选择,更多类型的生活方式,以及更多的发展可能性,进而走出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。
营会中,这种看见是双向的,结营展时,孩子们以小组为单位向参展者呈现着自己的“展品”,自己和伙伴这7天的经历与回忆。
孩子们将过程经历与活动产出转化为展览,邀请营员和村民成为观众,像人类博物馆的志愿者那样介绍与交流。
看到观展者认真聆听的表情、好奇或赞赏的眼光,拍照留念的动作时,孩子们也体验到了人类博物馆志愿者的感受:即自身叙事对他人生命带来影响的涟漪。
图为2024郝堂冬季营结营展上孩子向郝堂村民杨二姐介绍小组经历
启行学社的“人类博物馆”,是带动更多元的志愿者参与服务的尝试探索。它通过志愿者角色的剥离、生动的个体、流动的标签、对话的重构,试图回答公益领域的元问题:如何让服务成为主体共生的土壤。
当孩子们在标签中看到“自我定义的勇气”,在对话中体验“真理的复数性”,在展览中感受“叙事联结他者”的力量时,营会就有了自身的伦理的基础。——不承诺拯救,而是播撒理解;不提供完美的榜样,而是展示生命的真诚。
期待启行学社-人类博物馆一直存在,期待更多流动的新老“展品”持续参与营会,和孩子们一起用对话创造一个虽然小但属于双方的公共空间。
在此鸣谢所有曾在启行学社成为“人类博物馆”展品的志愿者们,感谢你在繁芜的世界,坚持保有作为具体个人的鲜活独特性,更感谢你把自己作为方法,用流动的对话,为河南的孩子打开一扇窗,看见更广阔的世界。